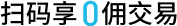在新的市场组织与竞争形势下,(针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的)传统监管理论与方法越来越捉襟见肘,监管当局也在尝试着更为先进的监管理念与策略。综合相关的讨论,这些转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关注市场结构转向关注反竞争行为。二是由寻求社会福利最优转向寻求满意状态。三是由一般性判别标准转向“一事一议”。四是由单纯的经济效率标准转向社会伦理标准。五是由简单的禁止性措施转向更为精巧的市场/监管机制设计。
虽然监管策略转向的意愿和趋势已经初显,要真正实现仍面临许多困难。其中之一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不完备性。二是精细化监管策略对于监管者专业能力的高要求。三是复杂监管策略的可实施性。四是监管政策中的公共选择问题。
大型互联网平台监管的一个政策焦点是反垄断问题。目前,相关议题的讨论绝大部分集中于平台基于市场地位的不当行为及其后果(如刘云,2020)和平台垄断地位的界定与市场权力的测度(如 OECD,2018)方面,对于垄断概念本身在平台治理中的适用性则涉及甚少。
然而正如诸多文献所指出的,大型互联网平台所代表的金融科技与网络经济的结合是一种新的社会生产乃至生活组织方式,其分析和治理需要相关经济理论基础的进一步深化和重构。基于此,我们将对垄断与市场结构合理性概念的经济理论基础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并由此引出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监管复杂性的思考。
垄断与市场结构合理性概念的经济学基础
市场结构合理性及相应垄断问题的经济学基础是市场失灵,而后者又可以追溯到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实际上,由于生产技术的凸性假设和对于企业主体的忽略,至少阿罗-德布鲁框架上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并未对市场结构有特定的要求,因此垄断的危害并不在于市场份额的不“平衡”,而在于厂商可能利用其市场地位扭曲产品价格,使得它不等于边际成本,而要素价格也因此不等于边际产出。换句话说,如果厂商能够安分守己地按照边际成本定价,那么市场结构或垄断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因而边际成本是更为关键的指标。值得注意的是,要素报酬等于边际产出、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这两个镜像条件对于某些经济学派而言不仅仅是评价市场效率的标准,也是收益分配公平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因此即使厂商偏离边际成本的定价行为不影响经济效率(如特定条件下的完全价格歧视),也仍然是不可接受的。这一点大大强化了市场结构在产业政策中的地位。
然而考虑到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和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这一条件对于市场监管者而言并不是一个可操作的标准,加上自亚当·斯密以来对于厂商面对超额利润时市场操守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使得市场结构成为了更为普遍的替代标准。在大部分情况下,评估市场结构只需要依托公开信息,并且有着成熟的客观技术指标,非常适于政策操作。这些便利成就了产业组织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实际上,SCP范式居于主导地位的20世纪50至80年代也是市场监管者的“黄金时代”,市场结构这一标尺不仅使得反垄断政策(相对于后来的“混乱时代”)简便易行,也给了监管者道义上的自信。
当然正如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所记述的,SCP范式一直饱受争议。其主要的批评者包括芝加哥学派、可竞争市场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等等。芝加哥学派强调市场结构是(效率驱动的)市场竞争的结果而非约束条件,可竞争理论认为市场的自由进入比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更为关键,新制度经济学则基于交易费用为企业兼并行为给出了非合谋动机的“合理”解释。虽然这些争论的焦点看起来是理论假设和范式上的分歧,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关于市场有效性的信念之争。在实证研究尚不能就何种理论更符合现实作出判断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和惯性决定了争论的走向,使得SCP范式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直至20世纪80年代基于博弈论的“新产业组织理论”(Tirole,1988)兴起,这种状况才发生改变。
新产业组织理论获得学界的主导权,除了其理论对于厂商行为更强的解释力以及理论范式的包容性之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西方市场自由主义的回潮,这大大削弱了SCP范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尽管如此,SCP仍然在经验实证和政策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学术领域,虽然新产业组织理论发展出了自己的经验实证技术,但是其研究数量与广泛性仍不能和基于SCP范式的经验实证相比。在政策领域,监管者们也发现新产业组织理论远不如SCP范式那么便捷易用(Jacquemin,2000),尤其是它缺乏市场结构这样的可操作标准,需要依赖大量关于厂商生产与管理的隐含信息,并且关于厂商行为的福利效应判断不仅取决于特定市场情境,还对市场参数高度敏感。在这种情况下,SCP范式仍然被保留作产业监管的传统工具。
鉴于本文的主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直至目前仍有不少研究基于SCP范式对于金融市场结构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但相对于实体经济领域的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由于流动性创造机构的存在,金融活动的“生产技术”并不满足凸性条件,竞争性金融市场的效率也没有瓦尔拉斯均衡存在性这样的基础性定理作为保障。事实上,即使是在局部均衡的框架中,竞争性金融市场的效率通常也未必是最优的(如Stiglitz and Weiss,1981)。而在考虑系统性风险等因素之后,简单的市场结构指标更是远远不足以支撑金融监管的政策决策。因此与金融领域的关联构成了大型互联网平台监管的一个重要复杂变量。
市场结构在什么情况下
不是一个好的监管标准
在理论上,一旦某个经济体的技术与偏好特征不符合凸性假设,或者市场中存在明显的交易费用,那么竞争性市场结构与运行结果的帕累托最优性质之间就失去了关联,换句话说,市场结构不再能够作为判断市场效率的标准。但是鉴于这一条件过于抽象与苛刻,下面我们将列举一些与大型互联网平台监管高度相关的市场情境,并讨论其中市场结构的(非)效率含义。
首当其冲的是存在创新行为的动态情形。为了给予厂商创新的动力,即使知道垄断可能会带来定价扭曲,政府也常常不得不授予创新者一段时期的垄断地位,以使其获得足够的收益来充分覆盖创新的成本。实际上,有观点认为创新者从专利垄断中获得的收益远远低于创新的社会收益,因此创新激励在总体上是不足的(如Romer,1993)。对于金融科技创新驱动的大型互联网平台而言,许多产品、业务模式甚至平台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并且以巨额的投资为代价,如果事前得知无法获得相应的专有收益,那么这些创新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进而从根本上影响相关消费者福利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是当市场存在搜寻成本的情形。如果消费者不能够无成本地找到市场中价格最低的卖家或者质量特征与自己的需求相吻合的产品,那么交易的达成就需要一个搜寻与匹配过程,这时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通常不是最优的。一种常见的可能是大量涌入市场的厂商会提高消费者找到合意产品的搜寻成本,就如我们在淘宝搜索商品时,得到的搜索结果经常充斥着无关的商品,而想要的商品反而被埋藏在数十个页面之后,这意味着新厂商的进入对于既有厂商造成了非价格外部性,从而使得竞争市场中的厂商数量高于最优水平。另一种典型情况是厂商有着自己的忠诚客户群且无法实施差别定价,这时如果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它们难以吸引到足够数量的其他客户群体,它们就会提高价格,以忠诚客户群的利益为代价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如Rosenthal,1980)。
再次是双边或多边市场的竞争情形。这也是大型互联网平台监管的焦点问题。网络效应本身很可能产生类似自然垄断这样的市场在位者优势,使得可竞争市场条件失效。不过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显示,通过适当的协调策略,具有更高效率的进入者也可以化解在位者的网络效应壁垒,成功进入市场甚至取而代之(如Ochs and Park,2010)。在现实的高技术公司竞争中,我们也见到了许多市场“巨无霸”被“独角兽”掀翻的例子。这些理论分析和案例显示,网络效应对于市场竞争的影响很可能被高估了。而双边乃至多边市场以及其中的复杂定价模式则使得市场结构对于效率的影响更为错综复杂,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带来价格的下降和消费者福利提升的情况并不鲜见(如Chandra and Collard-Wexler,2009)。不仅如此,在基于双边或多边市场的平台经济中,排他性定价、捆绑销售、合谋等传统“反竞争行为”的价格与社会福利效应也是不确定的(Jullien and Sand-Zantman,2021),这也给监管带来了极大困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的市场结构分析中,不同均衡的效率通常是帕累托意义上可比的,因此我们能够对于市场结构的社会福利效应给出清晰的判断。但是在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监管中,考虑到双边与多边市场的存在,不同市场结构经常会对应着帕累托不可比的均衡,其中不同维度的市场主体有着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如Song,2021)。这时监管当局不仅存在社会福利判断上的技术困难,还要面对不同监管策略的公共选择问题。
监管策略的转向及其中存在的困难
在新的市场组织与竞争形势下,传统监管理论与方法越来越捉襟见肘,监管当局也在尝试着更为先进的监管理念与策略。综合相关的讨论,这些转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关注市场结构转向关注反竞争行为。这是芝加哥学派一直以来强调的观点。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到,在双边或多边市场中,厂商行为与社会福利效应的关联要比市场结构更为密切,因此也是比后者更为可靠的监管“锚”。
二是由寻求社会福利最优转向寻求满意状态。传统监管手段对于市场结构的干预,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们需要达到满足社会福利第一定理的状态,也即帕累托最优。事实却是,假如技术和偏好都不满足凸性条件,实际上最优均衡是不存在的,基于这一目标制定监管政策也就成了空中楼阁,这种情况下只能寻求次优目标,即“满意解”。
三是由一般性判别标准转向“一事一议”。传统的SCP范式提供的是一般性的判别标准,监管当局只需要关注市场结构指标,但是在市场结构与市场效率脱钩并且新产业组织理论无法提供替代性通用判定指标的情况下,监管当局只能根据特定的市场状态、厂商具体的行动策略来考虑应该采用怎样的监管策略。相应地,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也更类似于由基于不同假设和行为框架的模型构成的案例集,为特定情形中的社会福利效应判断提供支持。
四是由单纯的经济效率标准转向社会伦理标准。这一转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监管当局和公众越来越关注各类监管政策的非经济效应,如收入分配、服务可及性、隐私保护等等; 另一个方面则是,大量“尾部”客户群体的存在使得公众更为积极地参与到传统上被认为属于经济专业领域的监管政策制定中,这也迫使监管当局更多地考虑监管政策的公众反应。
五是由简单的禁止性措施转向更为精巧的市场/监管机制设计。这种转变源于两个层面的因素:一个层面是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禁止经营、强迫分拆等传统监管手段不仅难以收到良好效果,还容易引发公众舆论的不满,迫使监管当局采用更为精细的策略;另一个层面的因素则是拍卖等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为监管当局提供了可选的工具。
不过虽然上述监管策略转向的意愿和趋势已经初显,要真正实现仍面临许多困难。其中之一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不完备性。目前关于平台经济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起步,许多重要问题都尚未得到解答,甚至没有明确的方向,这就使得监管政策失去了理论支撑。与此紧密相连的问题是,在平台竞争情形中,社会福利后果对于市场与技术初始状态高度敏感,许多模型的假设只是具有细微的差异,厂商行为的社会福利含义就截然不同。而在现实当中,要判断哪种模型假设更接近现实存在着很大困难,这也导致了监管者的茫然。
二是精细化监管策略对于监管者专业能力的高要求。与传统监管方式下只关注市场结构指标不同,高度精细化的“一事一议”监管方式要求监管者基于最新的经济理论对于当前情境下的市场状态和厂商行为及其效应作出准确的判断,这种标准即使专业领域的学者也很难达到。在产业组织领域存在着许多模糊或迷惑性的情形,如看似促进竞争的最低价格匹配策略实际上是标准的合谋手段,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监管者极容易被误导。引入专家证人可以部分地缓解这一问题,但是专家资源的可得性与相关的监管成本则又成为新的难题。
三是复杂监管策略的可实施性。虽然在公共资源的拍卖和公共部门规则等方面,制度设计已经有了许多成功的案例,但是失败的例子也并不鲜见。大部分制度设计都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但现实中的市场参与者经常达不到模型中假设的“理性”程度,例如不能正确理解与预测相关行动策略的收益和可能达成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监管策略反而不如简单直接的手段有效。
四是监管政策中的公共选择问题。如前所述,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厚尾”客户分布结构使得监管当局必须更多地考虑公众对于监管政策的反应。当监管政策可能涉及不同市场群体的利益分配,如网约车司机与乘客、外卖送货员与顾客、电商的买家和卖家等等,情况就会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监管当局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来平衡这些群体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理论上的“卡尔多补偿”实际是不可实施的。另一方面,由于公众并非经济领域的专家,在复杂市场条件下他们很难正确理解监管政策对于自身利益的影响,甚至可能抵制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措施,这就要求监管当局具备更强的政策沟通能力。

结语
大型互联网平台伴随着金融科技的兴起给市场监管部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要实现对于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有效监管,不仅要求监管工具的改革与完善,还有赖于经济理论,尤其是产业组织理论的进步。从目前的情况看,政策与理论两个领域的进展都还没有达到应对挑战的要求,这也引发了一些不安和焦虑。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太阳底下无新事”,当前热议的双边市场、长尾客户、网络效应等诸多现象,在历史上都曾经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通讯成本的下降而以各种形式出现过,并最终被接纳为市场的常态。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应该对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市场自我完善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同时对于不断涌现的创新给予高度的重视,在不断探索中找到政府与市场的正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