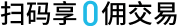文|翟巍
华东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在强化反垄断监管的背景下,超大型平台企业唯有在从事市场经营活动中循法而行,依法厘定自身施行平台治理行为的法定空间,才能避免承担法律责任,并为实现互联网经济行稳致远的发展目标提供助力。
1月13日,腾讯公司旗下的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对第三方违规导流链接的处理公示,以相关产品外部链接存在违规为理由,对QQ音乐、QQ浏览器、多多直播、知乎、好看视频、小红书等多个产品的外部链接进行限制处理。微信这一封禁行为引发质疑者与赞同者的观点论争。
究其实质,该项封禁行为是由微信这一超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实施的单方平台治理行为。由此引出的基本法律问题是:“作为超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微信是否有权实施封禁相关产品外部链接的严苛治理行为?如果它有权实施,本案中微信平台的治理行为是否违反比例原则?”
一、超大型平台企业不应越俎代庖施行公权力机关职责
与域外的脸书、亚马逊、谷歌平台一样,腾讯旗下的微信平台具有互联网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的角色。具体来说,由于涉及即时通信、社交媒体、电子商务、搜索引擎等领域的这类底部生态平台,被海量的市场经营者与消费者高频率与全方位使用,并已经构成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交易的主要联通渠道,因而经营者对这类平台服务产生高强度黏附性与依赖性。进一步而言,这类底部生态平台具有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必要设施”属性;除非这类底部生态平台的运营方准许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入驻其平台”并保持“在平台上的可见性”,否则其他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将处于严重劣势,甚至面临“功能性死亡”的结局。
在上述封禁案件中,作为“守门人”的微信平台以影响用户体验为由针对所谓的第三方违规导流链接实施限制处理。然而,该项平台治理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颇值得商榷。
其原因在于,在“流量为王”与“赢者通吃”的互联网经济领域,如果网络产品、服务的经营者不被允许经由微信平台分享而实施导流行为,那么经营者将被迫面临两难境地:如果经营者放弃使用微信平台,那么经营者将丧失与消费者交易的主要联通渠道,最终其网络产品、服务可能面临“功能性死亡”的前景;反之,如果经营者继续使用微信平台,但不再进行导流行为,其网络产品、服务将被迫内化于微信平台系统,最终将进一步巩固微信平台的垄断地位,导致互联网市场竞争机制的疲弱化与形骸化。
退一步而言,即使个别网络产品、服务确有损害微信用户体验的行为,微信平台运营方亦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通过寻求执法机关监管介入或提起司法诉讼的方式,促使这类网络产品、服务的经营者矫正相关行为,而不应越俎代庖施行公权力机关职责。
换言之,微信平台不应用自身制定的杂糅本位利益考量的平台治理规则取代监管法律法规,更不应对相关网络产品、服务实施生杀予夺式的严苛的拒绝交易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承担“守门人”角色的平台经营者滥用平台力量越界监管问题,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最近曾做出严正表态:“对数字世界的监管不能由数字寡头来完成。”
二、超大型平台企业不应违反作为“守门人”的公共义务与社会担当
互联互通属于互联网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虽然超大型平台企业是作为“准公共空间”的底部生态平台的运营者,但这类平台企业不应公器私用,逾越法律界限将底部生态平台作为排斥、打击竞争对手的私人禁脔。
进一步而言,如果作为“守门人”的超大型平台企业能够确保其平台运营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主动促成其平台与其他经营者网络产品、服务的互联互通,那么就可以强化网络产品、服务供给的多元属性,从而为用户设定更为宽广与弹性的选择空间,这无疑有利于增加消费者福祉与社会公共利益。
基于维护消费者福祉视角,微信平台以维护用户体验为理由封禁相关产品外部链接,不仅涉嫌违反比例原则,其目的与手段之间具有显著不匹配性,而且还产生一个明显的逻辑悖论。
具体来说,微信平台封禁相关产品外部链接,不仅将显著降低具有产品多栖性的用户的使用体验,而且涉嫌损害用户的通信自由,导致用户承担不必要的产品转换成本;基于此,微信平台实质上是采用“显著损害用户体验与利益”的手段来实现所谓的“维护用户体验与利益”的目标。
从更宽广的纵向视角分析,微信平台对竞争对手的网络产品、服务,实施屏蔽、封禁行为由来已久,且呈现模式化与系统化特征。虽然微信平台以维护用户隐私安全与加强平台生态治理为理由,试图论证此类屏蔽、封禁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却始终难以提供具有确凿性与可验证性的证据材料。基于此,兼具规则制定者、竞争者、裁判者身份的微信平台实质上是以“一言堂”方式,通过自订规则与自我宣示的手段屏蔽、封禁竞争对手的网络产品、服务。
这类延宕数年的屏蔽、封禁行为不仅违反公平竞争原则,显著压缩竞争对手网络产品、服务的生存空间,导致域内互联网经济呈现割裂化的孤岛效应,而且显著损害广大消费者的用户体验,人为增加消费者的转换成本。举例而言,早在2019年,微信用户张正鑫因发现无法通过微信向好友直接分享淘宝、抖音网页链接,就曾以腾讯拒绝交易为由将其告上法庭。
三、强化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监管背景下超大型平台的多维治理机制
迄今为止,欧美立法机关、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均不同程度地强化对于超大型平台企业滥用平台治理权限施行垄断行为的监管。
例如,在2020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脸书公司案件中,联邦贸易委员会指控的三宗罪就包括脸书公司滥用平台力量拒绝互联互通的行为。又如,欧盟最近公布关于互联网平台治理的《数字服务法(草案)》与《数字市场法(草案)》。依据这两部草案规定,由于超大型平台企业被视为数字市场的“守门人”,因而它们必须额外承担附加义务,以确保互联网竞争环境的开放性与公平性。举例来说,超大型平台企业被要求“允许第三方主体提供的服务与超大型平台企业的自有服务进行交互式操作”。
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监管范式由“包容审慎监管”演进到“全面强化监管”的背景下,微信平台等超大型平台不仅应当摒弃滥用平台治理力量排除、限制竞争的现行经营模式,而且应当切实承担其作为互联网市场“守门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主动采取措施促进自身平台在数字市场运营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如果微信平台等超大型平台能够果断放弃屏蔽、封禁竞争对手网络产品、服务的垄断行为,并在全面调研与充分听证的基础上设定新的能够兼顾各方合法权益的平台治理协议,那么这无疑将显著推动中国互联网经济由“野蛮生长”到“健康有序生长”的战略转型。
此外,由于超大型平台企业在单方实施平台治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缺乏客观性与中立性的弊端,由市场监管机关与第三方主体实施外源性与穿透式监督亦势在必行。
具体来说,超大型平台治理的基本架构可以被重新设定为“内置的平台自我治理+市场监管机关监督治理+第三方主体协同共治”的多维治理机制,该项机制应当涵盖违法行为处理听证机制、内部申诉机制、争议纠纷解决机制等子机制。其中,协同共治的第三方主体成员可以包括使用平台的企业用户、行业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中国相关公权力机关亦有必要依据《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市场监管法律法规,采行聚类分析与统计度量的实证方式,逐步设定具有可量化性、可验证性与可操作性特征的超大型平台综合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从而为超大型平台的多维治理机制提供可得统一适用的判定标准与参考指标。